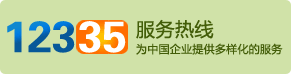
关于我们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是商务部免费为地方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窗口,基本职能是针对我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开展境外商务活动过程中遭遇的经贸摩擦、不公平待遇和商业欺诈等,免费提供公共信息、咨询指导并受理投诉,维护我境外商务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联系方式

电话:010-12335
邮箱:12335@mofcom.gov.cn
网址:12335.mofcom.gov.cn
邮箱:12335@mofcom.gov.cn
网址:12335.mofcom.gov.cn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91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91号